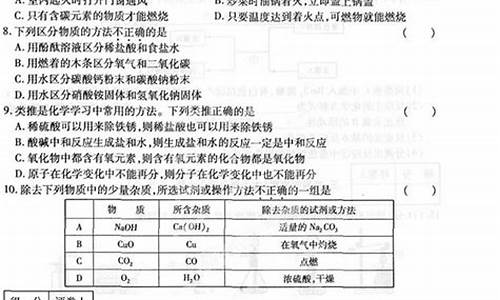临安贵金属交易公司_杭州临安黄金回收店地址
1.西北汇刊社的历史,谁知道,谢谢。
2.中国古代宋朝金融发展史
3.秦汉和隋唐比较 需要完整详细的资料
4.为何古代铜钱还不如铜值钱?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宋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盛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的扩大,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都在急速扩大。史实表明,宋代在工商业文明因素急剧成长的历史环境中,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据许惠民先生的研究,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已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并用作工业能源(如炼铁、烧瓷)是在北宋,其时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且有考古发掘为证。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专指煤炭。《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之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据估计北宋铁的年产量在3.5万吨到15万吨之间,接近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14.5万吨至18万吨的水平);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鍒”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获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
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刷新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帐,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显然来去自由。
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7个省份和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南朝鲜学者崔淳西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而且产品“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
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如浙东金华是“城中民以织作为主,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卷13161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再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表丝花钱物”等惯例⑥,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五是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同样是民营作坊占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亦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详情细节请参阅拙著相关章节。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造纸、印刷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二、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西北汇刊社的历史,谁知道,谢谢。
宋朝的经济
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③。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史实表明,宋代在工商业文明因素急剧成长的历史环境中,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④。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据许惠民先生的研究,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已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并用作工业能源(如炼铁、烧瓷)是在北宋,其时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⑤,且有考古发掘为证⑥。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专指煤炭。《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之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据估计北宋铁的年产量在3.5万吨到15万吨之间,接近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14.5万吨至18万吨的水平⑦);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鍒”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早在1959年,柯昌基先生即据神宗元丰年间苏轼的《徐州上皇帝书》指出,徐州附近利国监所辖“三十六冶”中已经产生雇佣关系①。据苏轼所言,这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场气象;各冶炉主“藏镪巨万”,可见资本雄厚;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冶户皆有“失业之忧”;不久取消禁令,“使铁北行”,冶户“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③,反映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土地,而且多半已从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无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获得了“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处分”③的权利。
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获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④。
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刷新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⑤。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帐,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⑥,显然来去自由。
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7个省份和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⑦。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⑧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①。南朝鲜学者崔淳西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而且产品“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②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
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③,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如浙东金华是“城中民以织作为主,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④)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卷13161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再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⑤。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表丝花钱物”等惯例⑥,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五是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同样是民营作坊占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亦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详情细节请参阅拙著相关章节。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造纸、印刷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二、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我的认识是“三缺一”,即四个条件中具备三个,还缺一个。
一是在人口增长(北宋徽宗时人口达到1亿,较汉唐增加1倍)的压力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扩大速率,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被迫另谋生计,大量进入城市和工商业领域。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这些非农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根据我的计算,宋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汉代提高1倍,比唐代提高30%,与年每劳生产4379斤大致相当①。这个成就的取得,与宋代耕作制度的变革有关。大约在两宋之交,即12世纪上半叶,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福建沿海,还有江西中部的吉泰盆地等农业区,一年两熟的复种制作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②。各路平均而计,复种指数约为134%左右③。粮食产量的提高也为经济作物的种植腾出了更多的耕地,东南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在逼迫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苎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当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自然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于是专业茶农、蔗农、果农、菜农大批涌现,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二是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的兴起。诸如炼钢工艺中灌钢法的推广,冶铜工艺中胆铜法的发明,金属加工工艺中“旋作”(即简易车床)的使用,掘井工艺中以“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技术,纺织工艺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轴架整经法的使用,造船工艺中水密舱的发明,还有航海罗盘的使用,造纸业中竹茎等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以及印刷工艺中雕版的推广和铜版、活字版的发明等,都是其时之茕茕大者。其详情细节笔者曾有专文论及,此处不赘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成果最丰、成就最大、进展最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时期,不仅超过汉唐盛世,而且为此后的明清所不及。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从中不难看到宋代工匠从手工劳动逐步走向机器生产的精巧构思与卓绝努力。
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自中唐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份趋于瓦解,乡村主户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权基本分离,而地权集中与地块分散的背离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⑤。在这样一些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仆之类的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人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正如我们前面在矿冶、井盐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都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宋代不仅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而且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增加,城市性质发生嬗变。汴京、临安作为首都已是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虽然仍是政治、军事中心,但其工商业依然极为繁盛⑥。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前述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作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亦属此类性质;前述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这是盐业城镇;举世闻名的江西景德镇有陶工数千人,这是陶瓷城镇。至于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南宋时“生齿无虑五十万(口)”①。
城市的增多及其商业意义的增长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加快了城郊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步伐(如茶农、果农)。同时城中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还有服务行业的发展则为雇佣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壤沃土。作为这一切的重大结果,便是城镇(含矿区、港口)市民阶层的勃兴。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冶家”、“磨户”、“茶培主”,还有“行老”、“市头”(以上为一方),以及“杂作工匠”、“裨商细贩”、“百姓绣夫”、“游手末作”(以上为另一方)等,就是这个阶层的基本成份。就是被人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重要表现的市民、矿工斗争,宋代亦有端倪可鉴。前述井研县“佣身赁力”之盐工一不如意就“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可算经济斗争;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安徽舒州宿松矿工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有众五百余”②则是武装斗争性质了。如所周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雇佣关系发展和市民阶层初兴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视为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条件的共同支撑,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才会取得如上所述的种种进展。遗憾的是这个进程并未结出现代化之正果,直接的原因当然可以归之于战争的干扰。12世纪初女真铁骑频频南下,饮马黄河;接踵而来的13世纪由蒙金战争拉开帷幕,继之以宋蒙(元)战争,中原、江南屡遭战祸蹂躏。其后虽在元朝统治下复归统一,但领主分封制、匠局制(实即工奴制)和“驱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在更广阔的地域内死灰复燃(原先大致局限在辽夏金辖区),要到明初开国数十年才重新回到宋代开启的历史轨道上来。这就是说,自北宋末年开始,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段内,原始工业化进程因屡遭打击而奄奄一息。
中国古代宋朝金融发展史
宋朝的经济
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③。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史实表明,宋代在工商业文明因素急剧成长的历史环境中,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④。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据许惠民先生的研究,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已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并用作工业能源(如炼铁、烧瓷)是在北宋,其时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⑤,且有考古发掘为证⑥。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专指煤炭。《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之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据估计北宋铁的年产量在3.5万吨到15万吨之间,接近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14.5万吨至18万吨的水平⑦);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鍒”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早在1959年,柯昌基先生即据神宗元丰年间苏轼的《徐州上皇帝书》指出,徐州附近利国监所辖“三十六冶”中已经产生雇佣关系①。据苏轼所言,这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场气象;各冶炉主“藏镪巨万”,可见资本雄厚;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冶户皆有“失业之忧”;不久取消禁令,“使铁北行”,冶户“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③,反映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土地,而且多半已从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无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获得了“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处分”③的权利。
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获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④。
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刷新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⑤。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帐,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⑥,显然来去自由。
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7个省份和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⑦。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⑧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①。南朝鲜学者崔淳西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而且产品“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②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
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③,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如浙东金华是“城中民以织作为主,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④)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卷13161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再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⑤。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表丝花钱物”等惯例⑥,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五是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同样是民营作坊占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亦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详情细节请参阅拙著相关章节。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造纸、印刷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二、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我的认识是“三缺一”,即四个条件中具备三个,还缺一个。
一是在人口增长(北宋徽宗时人口达到1亿,较汉唐增加1倍)的压力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扩大速率,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被迫另谋生计,大量进入城市和工商业领域。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这些非农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根据我的计算,宋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汉代提高1倍,比唐代提高30%,与年每劳生产4379斤大致相当①。这个成就的取得,与宋代耕作制度的变革有关。大约在两宋之交,即12世纪上半叶,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福建沿海,还有江西中部的吉泰盆地等农业区,一年两熟的复种制作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②。各路平均而计,复种指数约为134%左右③。粮食产量的提高也为经济作物的种植腾出了更多的耕地,东南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在逼迫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苎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当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自然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于是专业茶农、蔗农、果农、菜农大批涌现,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二是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的兴起。诸如炼钢工艺中灌钢法的推广,冶铜工艺中胆铜法的发明,金属加工工艺中“旋作”(即简易车床)的使用,掘井工艺中以“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技术,纺织工艺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轴架整经法的使用,造船工艺中水密舱的发明,还有航海罗盘的使用,造纸业中竹茎等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以及印刷工艺中雕版的推广和铜版、活字版的发明等,都是其时之茕茕大者。其详情细节笔者曾有专文论及,此处不赘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成果最丰、成就最大、进展最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时期,不仅超过汉唐盛世,而且为此后的明清所不及。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从中不难看到宋代工匠从手工劳动逐步走向机器生产的精巧构思与卓绝努力。
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自中唐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份趋于瓦解,乡村主户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权基本分离,而地权集中与地块分散的背离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⑤。在这样一些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仆之类的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人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正如我们前面在矿冶、井盐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都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宋代不仅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而且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增加,城市性质发生嬗变。汴京、临安作为首都已是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虽然仍是政治、军事中心,但其工商业依然极为繁盛⑥。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前述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作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亦属此类性质;前述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这是盐业城镇;举世闻名的江西景德镇有陶工数千人,这是陶瓷城镇。至于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南宋时“生齿无虑五十万(口)”①。
城市的增多及其商业意义的增长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加快了城郊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步伐(如茶农、果农)。同时城中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还有服务行业的发展则为雇佣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壤沃土。作为这一切的重大结果,便是城镇(含矿区、港口)市民阶层的勃兴。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冶家”、“磨户”、“茶培主”,还有“行老”、“市头”(以上为一方),以及“杂作工匠”、“裨商细贩”、“百姓绣夫”、“游手末作”(以上为另一方)等,就是这个阶层的基本成份。就是被人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重要表现的市民、矿工斗争,宋代亦有端倪可鉴。前述井研县“佣身赁力”之盐工一不如意就“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可算经济斗争;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安徽舒州宿松矿工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有众五百余”②则是武装斗争性质了。如所周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雇佣关系发展和市民阶层初兴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视为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条件的共同支撑,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才会取得如上所述的种种进展。遗憾的是这个进程并未结出现代化之正果,直接的原因当然可以归之于战争的干扰。12世纪初女真铁骑频频南下,饮马黄河;接踵而来的13世纪由蒙金战争拉开帷幕,继之以宋蒙(元)战争,中原、江南屡遭战祸蹂躏。其后虽在元朝统治下复归统一,但领主分封制、匠局制(实即工奴制)和“驱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在更广阔的地域内死灰复燃(原先大致局限在辽夏金辖区),要到明初开国数十年才重新回到宋代开启的历史轨道上来。这就是说,自北宋末年开始,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段内,原始工业化进程因屡遭打击而奄奄一息。
秦汉和隋唐比较 需要完整详细的资料
宋代的金融(上)
邓高峰
金融,简言之即资金的融通。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规模庞大的货币资本运动,因而金融早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历史地看,金融又是一个很古老的部门与行业。今年高考语文(河南卷)现代文阅读试题,是一篇关于宋代金融与信用的短文,文章在娓娓道来中勾勒了宋代信用的形式、特点及其作用。其实,在中国古代金融发展史上,宋代金融及其信用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一方面续写着中国古代金融发展的新篇,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深刻教训。
币制的整顿
唐灭亡后,中国陷入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五代政权都以正统自居,因而都铸造自己的货币,十国中的前蜀、楚、闽、南汉、后蜀、南唐也都曾发行货币,铸有铜钱、铁钱、铅锡钱等,其中以铁钱为多,加上民间私铸恶钱屡禁不止,因而这一时期的货币币材低劣、币种多样、币值波动不定,流通具有割据性、封闭性。政权的林立导致货币制度各自为政,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十分混乱,就像回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因而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倒退。
北宋政权建立后,就着手对货币进行整顿,严禁私铸钱和劣币流通。《宋史》载,太祖时,“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公式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太宗时又下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整顿的结果是,除川、陕外,铜钱成为全国多地使用的货币,传统的铜本位币制再度确立。到真宗年间,铜币逐步取代了五代时的旧币。
为此,朝廷还规定了铜钱的配料和重量,各时期有所不同。如真宗景德年间,朝廷规定的铜钱铸造标准是,每贯(即1000文)用铜3斤10两、铅1斤8两、锡8两。
宋代的铸币机构,依唐旧制,也称钱监,分布于全国各地。因铸钱的币材不同,有铁钱监、铜钱监两大类,其中主要是铜钱监。
为保持对铜钱的绝对控制权,朝廷实行“铜禁”政策,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及冶炼,同时禁止民间储存铜钱或铜器,犯“铜禁”者严惩;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阻止铜钱外流。但是,由于以上政策收效有限,加之货币流通量的增加、铜钱的外流、民间的窖藏等原因,最终还是引发了闻名于历史的“钱荒”。对此《宋史》载:“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至于贵金属金银,其目的本不在日常交易流通,而是作为财富贮藏和大宗的支付手段。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朝廷就宣布禁止伪造黄金白银。政府将金银铸成金银铤,作为财富的代表而贮藏起来,铸造的金银钱则主要用于赏赐和喜庆。在对外贸易和与西夏、辽的关系中更是大量使用白银和绢帛。
北宋的交子
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它的产生就是为了方便商品的交换。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宋代货币成就的最大亮点。它的出现当然有其必然性。
北宋开国前后,四川普遍使用的是铁钱,真宗景德年间还铸造有大铁钱。铁钱体重大而价值小,“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可见铁钱自身的缺陷是“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
交子成为纸币有一个过程。最初交子是蜀地商人私自印行,属“私交子”,结果导致“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以治蜀著称的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张咏(字复之)进行整顿,令16家富户“连保作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张咏也因之有了中国“交子之父”的说法。这时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信用凭证,也可以说是一种代金券。交子出现后,因为随时可以变现,方便了交易,但随之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富户中有的“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形势逼迫着交子必须升格,由私人信用上升为政府信用。
天圣元年(1023年),时担任益州转运使的薛田、张若谷上奏朝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益州交子务在成都设立,次年开始发行交子,自此交子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正式发行流通,此为“官交子”。其面值最初为1贯到10贯,共10种。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起改为5贯和10贯两种。
交子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楮币”或“楮券”。据《宋史》载:“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这是因为印刷交子使用的是楮纸,一种用楮树皮为材料制造的纸张,而成都造纸业发达,楮纸制造精良,故用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戴蒙知绵州,又请求朝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交子的印制过程。
南宋的会子
会子原产生于北宋,有寄附会子、铅锡会子、钱会子、合同会子等多种,这里的“会”是兑、取之意,因此会子是一种有价证券或领取钱物的凭证,并非纸币。南宋初,都城临安民间也自发产生了便钱会子,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钱端礼知临安府,“命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东南用会子自此始”。自此,会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会子作为南宋纸币正式诞生。后钱端礼任户部侍郎,会子由户部接办。绍兴三十一年(1162年),设立“行在会子务”(后更名为“行在会子库”。行在,天子所在之地)发行会子,有1贯、2贯、3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会子。因发行机关为行在会子务、会子库,故会子称“行在会子”,又因为主要在东南流通,故又称“东南会子”。乾道四年(1168年),会子立界限额发行,“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
会子流通之初,由于有10万缗铜钱作准备金,会子币值坚挺。孝宗乾道以后,因宋金交战,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加上开始不设界发行兑换,发行额大增,会子一度贬值,对此辛弃疾曾上疏:“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宋金议和后,朝廷进行整顿,孝宗年间,定三年为一界,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以新换旧﹐会子的币值一直稳定。光宗绍熙年间以后,为筹措军费,会子发行量猛增,会子不断贬值。到理宗末年,恶性通胀愈演愈烈,两百贯会子买不了一双草鞋,几乎是一文不值,南宋的货币体系全面崩溃。对此,学者许衡曾批评说“无义为甚”。学者高斯得也说:“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
南宋的会子还有地方版,主要有湖广会子、两淮会子、银会子、铁钱会子等。理宗宝公式四年(1256年),朝廷改钱引为四川会子,直至宋亡。
钱引与关子
纸币的发行量是有限度的,过度发行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最初交子发行,以两年为一界,界满换发新交子,币值稳定。王安石变法后,货币需求量大增,加上西北边境军需开支,加剧了北宋钱荒。政府一方面增铸铜钱,另一方面,自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开始,交子两界并行流通。哲宗绍圣年间,交子“每岁书放亦无定数”,政府对于交子的发行已经开始失控。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发行42界交子,发行量有两万四百多万贯,相当于仁宗天圣年间的20多倍,交子陷于恶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令诸路更用钱引……时钱引通行诸路”。大观元年(1107年),“诏改四川交子为钱引”。由于发行随意,钱引继续贬值。南宋时,钱引继续流通,仍以两年为一界(后改为三年一界),发行量也继续增加,“增引日多,莫能禁止”,以至于“楮券日轻,民生流离,物价踊贵,遂至事无可为”。交子与钱引沦为政府攫取社会财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货币体系的全面崩溃。
南宋时期,还有一种称为“关子”(后称“见钱关子”)的纸币,最初由户部于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发行。其原因是婺州(今浙江金华)屯兵,需运军费,而都城临安“至婺州不通水路,难以津搬”,于是诏令户部“印押见钱关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执关子赴杭、越榷货务请钱……有伪造者,依川钱引抵罪”。关子的持有者可以到榷货务兑换现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官营汇兑。关子发行后,因为准备金充足,并可以随时兑现,所以信誉较高。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要求民间“依见缗用”(缗:1000文铜钱穿成一串叫1缗),关子遂成为纸币。后来还发行有“铜钱关子”“金银关子”以及湖广关子、淮西关子、随州关子等。
为保证关子的信用,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规定关子“听民间从便使用,即不得辄有减落。如有妄说事端、贱价兑买之人,主赏钱五百贯,许诸邑人陈告,其取旨从重断罪”。诏令关子不许私自贬值、贱价收兑,以保护关子作为货币的流通。到了南宋末年,财政困难,贾似道当权,乘理宗病危之机,发行金银见钱关子,物价急剧上涨。南宋亡后,关子与会子皆成为历史。
宋代的金融(下)
邓高峰
两宋金融机构
今天的金融机构,按地位和功能不同,分为银行和非银行(如保险、证券、信托等)两种。以此参照,在宋代的金融机构体系中,交子务、会子务可分别称为北宋和南宋的“银行”。因为如前所述,交子务是北宋掌管纸币印刷、发行事务的机关,会子务(会子库)则掌管南宋纸币的印刷、发行。除此之外,两宋的其他金融机构主要还有:
1.便钱务:宋代朝廷为了增加京师的铜钱储量以及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根据唐代飞钱办法,实行便换,称为便钱。太祖开宝三年(970年),京师设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至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也就是说,商人把钱纳入左藏库,得到取款凭证“券”,然后到经商的州县领钱,并且朝廷有信用的保证。这里的券相当于现在的定额支票。商人携带这种“支票”免去了携带大量现金进行交易的麻烦,因此便换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
2.榷货务:我国自古以来,多数朝代都实行禁榷制度,政府对重要商品如盐、铁、酒、茶、香料等实行垄断经营。宋代也如此,并且由于“三冗”(冗官、冗军、冗费)和外患的原因而得到强化。作为宋代的财经和金融机构,榷货务最早设立于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在京师和地方均有设立。除了在专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榷货务还承担了不少金融职能,概而言之有便钱,即现金汇兑。如景德三年(1006年),诏令:“客旅见钱往州军使用者,止约赴榷货务便纳,不得私下便换。”这是榷货务经营便钱的最早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因婺州屯兵,“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子于榷货务请钱”。在货币的兑换与回笼方面,徽宗时期,钱引取代交子后,手持交子者须到榷货务买钞所兑换钱引。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间,榷货务又承担了回笼纸币会子的功能。在政府收购粮草上,榷货务还负责拨款给地方政府,或者兑付地方政府为赊买粮草所发的信用证券。熙宁三年(1070年),“河北缘边,岁于榷货务给缗(
钱) 三二百万,以供便籴”。熙宁四年(1071年),“诏给榷货务封桩银十二万七千两、绢万七千匹,赴陕西转运司籴军储”。
3.市易司(务):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市易法(王安石变法之一)颁布实施,据此东京设都市易司,后在一些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市易务贷款商贾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年息两分,可见其主要职责是平抑物价、以通货财,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因而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除此之外,市易务也可召人抵当借钱出息,提供信用。哲宗元公式元年(1086年)废,绍圣四年(1097年)复置。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后再废。
4.质库:作为以财物作质押而进行借贷融资的一种方式,典当业也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两宋城市尤其是东京和临安,商品经济发达,融资活跃,因而典当业十分红火,官、民和寺院典当并行,并逐渐向专营发展。质库就是从事典当业、进行押物放款收息的金融机构。民营质库又称“解库”“典库”,寺院开办的质库叫“长生库”。《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家悬挂“解”字招牌的店铺即是典当铺。《东京梦华录》有“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的记载。南宋时民营质库更加普遍,都城临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官营质库叫抵当所(抵当库),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设立于京师,元丰七年(1084年)推行于诸路,属官营借贷机构,主要职责是“掌以官钱听民质取而济其缓急”,也即是经营抵押贷款,因而已具有今天商业银行的性质。王安石变法中的两个关于政府的法令,市易法和青苗法,前者规定,百姓可以用田地、房产和其他贵重财产作抵押向政府借款,年息两分,过期不赎纳利息,每月罚钱2%。后者规定,每年春天,农民可用秋收作保证,向政府借款,利率两分,期限半年,秋收后归还。
5.金银彩帛铺:北宋东京有一条集中经营金银、彩帛的街巷。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南通一巷”是指向南通往一条巷子,“界身”是这条街巷的名字。这是个什么地方?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这是个怎样的地方?“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这里的交易规模怎样?“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据此可以说,这里是北宋东京的金融一条街。因为北宋时期,金银和彩帛都是价值的代表。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就诏令:“禁伪造黄白金,募告者赏钱10万。”至于彩帛(彩色丝织品),与银一样,是北宋朝廷输辽、西夏的重要物资。
6.交引铺:交引是官府发给商人的商贸凭证,由交引库负责印发、收纳。榷禁制度的推行,商人经营茶、盐等,都需要先付出粮草或现钱,领取交引,再凭交引兑取现钱或政府专卖货物。“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因此宋代交引有茶交引、盐交引、见钱交引多种,交引也成为一种有价证券。有些持有交引的人愿意将它卖出,于是买卖交引的店铺即交引铺就应运而生了,其盈利当然来自于交引买卖的差价。南宋还诞生了金银交引铺,又称“金银盐钞引交易铺”“金银钞引交易铺”。据《梦粱录》载,南宋都城临安,“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由于交引买卖属大宗交易,交引经营者财力雄厚,所以交引铺里往往“前列金银器皿及见钱,谓之看垛钱”。官巷南街可以说是南宋临安的金融一条街。
7.检校库:这里的“检校”是官府为遗孤查核、登记、保管财产,因而检校库就是代管户绝没官财产和官员的孤幼应获得的父母遗产,其收益供被检校户的孤幼享用,类似于今天的信托机构。仁宗时期,朝廷专门在开封府设立检校库,到神宗时,检校库又以所保管的遗孤资产进行放贷,允许百姓从检校库贷款,所得利息收入用来补贴遗孤生活,于是检校库就有了融资的功能。
影响与教训
两宋时期,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共同发展,金融业务多种多样,信用工具不断创新,加上信用管理的制度化,因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币制的整顿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五代十国以来货币割据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纸币的产生及其流通解决了铜钱的短缺和铁钱的不便,加上货币的兑换、信贷业务的推行,这无疑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抵押、检校等业务的开展缓解了百姓的用钱难题,保证了生产的进行和生活的急需,也促进了社会优抚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各种金融票据的发行和纸币投放的增加也缓解了财政困难,增加了财政收入,等等。
但是,两宋金融留给后人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多方面的。首先,纸币发行、流通后,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反假币。两宋政府从精选用纸、印制复杂图案文字、使用多重印押防伪、进行多色套印、使用铜版印刷、定期换界流通等方面加大防伪技术,同时通过颁布法令、严惩造伪、重奖举报、失职追责等手段反假打假,但假币一直不绝,特别是两宋之交和南宋末年,伪造纸币横行,南宋理宗曾有“伪造之禁不严,真伪莫辨”的无奈。其中原因,除了不法之徒见利忘义、肆意妄为外,纸币滥发导致用纸质量下降、拖延换界导致纸币使用期限过长也是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保证纸币的信用,必须在不断提高防伪技术和印刷质量的前提下,加强金融法治和金融文化建设。
其次,金融业的发达同时也伴随着投机性、寄生性甚至是腐朽性的增加,货币兑换、典当抵押、高利贷的发放,无不存在着盘剥甚至是商业欺诈,这对社会弱势群体如农民、小生产者、小商人等非常不利。《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在神宗年间,赞同王安石变法的人曾言:“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不得。”即便是新法推行后,由于官吏舞弊等原因,执行的实际情况也不理想,对此苏辙曾言:“以钱货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因此,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对弱势群体的照顾。
当然,两宋金融留给后人最深刻的教训当是由于纸币发行的无序和无度而导致的信用危机以及币制与经济的崩溃。特别是两宋末年,面对庞大的军需开支和严重的财政危机,两宋政府往往通过滥发纸币来转嫁危机,加上发行准备金严重不足,因而导致了两宋纸币的巨额发行和政府对通胀的束手无策,其结果当然是经济的崩溃和人民生活的灾难,也动摇了自身政治统治的基础,加速了政权的覆灭。这告诉我们,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定要按照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对于金融,必须科学管理,做好对其风险的评估与管控。
引自:汴梁晚报
为何古代铜钱还不如铜值钱?
宋朝的经济
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③。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史实表明,宋代在工商业文明因素急剧成长的历史环境中,其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煤铁革命的发生和民营矿冶作坊中雇佣劳动的出现。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期④。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据许惠民先生的研究,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已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并用作工业能源(如炼铁、烧瓷)是在北宋,其时河东(今山西)、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⑤,且有考古发掘为证⑥。为了和原先的木炭(时称“软炭”)相区别,宋代出现了“石炭”、“矿炭”等词专指煤炭。《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四八有“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之语。
煤炭采掘业的兴起既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据估计北宋铁的年产量在3.5万吨到15万吨之间,接近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14.5万吨至18万吨的水平⑦);同时又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以“生熟杂鍒”为特征的灌钢法的大面积推广;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重大进展构成一幅宋代煤铁革命的壮观景象。
早在1959年,柯昌基先生即据神宗元丰年间苏轼的《徐州上皇帝书》指出,徐州附近利国监所辖“三十六冶”中已经产生雇佣关系①。据苏轼所言,这36个民营铁冶作坊,各有百余名工人,已具手工工场气象;各冶炉主“藏镪巨万”,可见资本雄厚;政府关闭河北市场(“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冶户皆有“失业之忧”;不久取消禁令,“使铁北行”,冶户“皆悦而听命”,可见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而总数达三四千名的冶铁工人多是“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③,反映他们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土地,而且多半已从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对国家,均无人身依附关系之束缚,获得了“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处分”③的权利。
二是川蜀地区民营卓筒井的兴起和雇佣工人的经济斗争。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首先出现在四川井研县的卓筒井,标志着钻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的过渡。它在钻井工艺上,首创“冲击顿挫法”,由熟铁钢刃所制的“圜刃”应是世界上第一个深井钻头,开近代凿口钻井技术之先河;在井壁成型技术上,首创“套管隔水法”,所用竹制套管(此即卓筒井得名之由来,卓、竹,一音之转)显然是明清木制导管和近代铜制导管的前身;在取屑工艺上,首创“活门式扇泥筒”;在汲卤工艺上,有“无底而窍”的汲卤筒取代原先的皮囊,入水自开,出水即闭。这些重大创获从各方面奠定了近代深井钻探技术的基本原理,因而被科技史界誉为现代“石油钻井之父”④。
正因卓筒井从本质上刷新了大口浅井的陈旧技术,在开凿成本、卤水质量、生产效益等各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所以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短短二、三十年间就遍布于川南陵州、嘉州、荣州一带,“连溪接谷,灶居鳞次”,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盐业史专家郭正忠先生依据神宗熙宁年间陵州知州文同的奏疏,证明四川井盐业中不仅同样存在着雇佣关系,而且还发生过为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⑤。据文同奏疏所言,当时井研县即有百余家筒井作坊,每间作坊分别雇佣“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这数千工匠多数来自“他州别县”,已与土地脱离关系;其谋生方式是“佣身赁力”,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受雇期间如对工作条件或待遇不满意,就互相串联,集体抗议,所谓“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如无改善即与井主“豪者”算帐,索取工资,所谓“算索工值,偃蹇求去”;再另谋高就,所谓“又投一处,习以为业”⑥,显然来去自由。
三是陶瓷业的商品生产性质及其日趋扩大的海内外市场。
陶瓷生产在宋代进入成熟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遍布全国17个省份和130余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窑性质⑦。特别是福建路的德化窑和晋江、厦门等地瓷窑,以及泉州磁窑,安溪、南安、同安等窑,则是泉州刺桐港大宗外销瓷器的生产基地。在有罗盘导航的大型“海舶”之上,“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⑧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多年沿海上丝路进行实地考察,于1979年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宋代瓷器在新加坡、印尼雅加达、越南西贡,印度迈索尔邦、马德拉斯邦,巴基斯坦的班布尔遗址,西亚伊拉克的萨马腊遗址,以及北非埃及的福斯坦特等地区的分布实况①。南朝鲜学者崔淳西说过,“朝鲜发现的中国瓷器,以宋瓷,特别是北宋产品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中南部沿海地区”,而且产品“几乎囊括了宋代所有名窑的制品。”②这说明宋代陶瓷业就其主体部分而言完全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而且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四是数万纺织机户的涌现和包买商惯例的形成。
宋代“机户”一般系由家庭成员充劳动人手,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其性质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也有少数机户实行雇工生产。据漆侠先生估计,北宋各路约有10万机户③,数量可观。问题是这些机户除少数在城市(如浙东金华是“城中民以织作为主,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④)外,多数分布在乡村,他们的产品需要中间人将之集中起来,运到市场上去,才能真正成为商品,于是包买商就出现了。《永乐大典》卷13161所载“陈泰冤梦”,即是反映江西包买商的典型事例,时在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2世纪70年代)。冤主陈泰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等地的机户发放生产性贷款(“贷出本钱”),到夏秋之际再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再向外运销。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驵主”、“甲首”作为放钱收布的代理人。仅乐安一地就“积布至数千匹”。从“如是久矣”看,这种做法早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⑤。这种做法在其本质特征上已与明清“帐房”无异,均属包买商惯例。郭正忠先生指出,在两浙丝织业、四川绫锦业中,也有“收丝放贷”、“机户赊帐”以及“预表丝花钱物”等惯例⑥,这说明宋代包买商分布地域广泛,江西、两浙、四川等地都可以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五是在制茶、造纸、印刷等行业中,同样是民营作坊占主导地位,从事商品性生产,拥有可观的市场,在其内部亦可见到雇佣劳动的存在。详情细节请参阅拙著相关章节。
通过以上的简要勾勒,我们看到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全方位的。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之下,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纺织、造纸、印刷等业在内的手工业各部门一度呈现出全面繁荣态势;民营手工业全面崛起,除铸钱、军工等少数行业外,其主导地位已确立无疑,并程度不同地拥有区域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海外市场;其间带有近代色彩的雇佣关系、包买商惯例亦在顽强生长。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为近代工业的发生准备条件的时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降临提供历史前提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前近代化时期。如果这个势头能够保持二、三个世纪不被打断的话,必将为其后的工厂(机器)工业化奠定坚实基础。
现在我们要问,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诸般条件,宋代社会是否具备呢?我的认识是“三缺一”,即四个条件中具备三个,还缺一个。
一是在人口增长(北宋徽宗时人口达到1亿,较汉唐增加1倍)的压力下,耕制革命的发生,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为原始工业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由于人口增长速率超过耕地面积的扩大速率,产生了大批无地或少地农民,他们被迫另谋生计,大量进入城市和工商业领域。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则为这些非农人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根据我的计算,宋代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粮食大致在4000斤上下。比汉代提高1倍,比唐代提高30%,与年每劳生产4379斤大致相当①。这个成就的取得,与宋代耕作制度的变革有关。大约在两宋之交,即12世纪上半叶,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苏皖平原和福建沿海,还有江西中部的吉泰盆地等农业区,一年两熟的复种制作为基本的耕作制度得以肯定下来②。各路平均而计,复种指数约为134%左右③。粮食产量的提高也为经济作物的种植腾出了更多的耕地,东南地区地狭人众的情况也在逼迫当地农户寻求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如苎麻、桑梓、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药材、花卉等。当产地周围存在着相应的市场时,生产者的着眼点自然会从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向它的交换价值,于是专业茶农、蔗农、果农、菜农大批涌现,商品性农业由是而发展起来。
二是煤铁革命的推动和海内外市场的扩大,导致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的兴起。诸如炼钢工艺中灌钢法的推广,冶铜工艺中胆铜法的发明,金属加工工艺中“旋作”(即简易车床)的使用,掘井工艺中以“卓筒井”为代表的小口深井技术,纺织工艺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轴架整经法的使用,造船工艺中水密舱的发明,还有航海罗盘的使用,造纸业中竹茎等硬纤维软化技术的成熟,以及印刷工艺中雕版的推广和铜版、活字版的发明等,都是其时之茕茕大者。其详情细节笔者曾有专文论及,此处不赘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成果最丰、成就最大、进展最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时期,不仅超过汉唐盛世,而且为此后的明清所不及。如此巨大的科技进步和工艺革新,显然是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内在动力。从中不难看到宋代工匠从手工劳动逐步走向机器生产的精巧构思与卓绝努力。
三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性质嬗变和市民阶层初兴。自中唐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转移率的提高导致累世相承的主仆名份趋于瓦解,乡村主户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行政统辖权与土地所有权基本分离,而地权集中与地块分散的背离则迫使部曲庄园制经营方式日趋衰落⑤。在这样一些经济变革趋势的推动下,宋代农民之主体确已挣脱了昔日部曲、宾客、徒附、私属、奴婢、佃仆之类的农奴地位,并日趋普遍地获得了迁徙和退佃等权利。他们一旦脱离土地,流人城市或矿区,就有可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正如我们前面在矿冶、井盐业中所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都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宋代不仅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而且随着城市商业意义的增加,城市性质发生嬗变。汴京、临安作为首都已是百万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虽然仍是政治、军事中心,但其工商业依然极为繁盛⑥。苏州、扬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处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前述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作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亦属此类性质;前述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这是盐业城镇;举世闻名的江西景德镇有陶工数千人,这是陶瓷城镇。至于广州、泉州、明州还有北方的板桥镇等则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为命”,南宋时“生齿无虑五十万(口)”①。
城市的增多及其商业意义的增长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加快了城郊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的步伐(如茶农、果农)。同时城中兼营工商业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还有服务行业的发展则为雇佣关系的成长提供了肥壤沃土。作为这一切的重大结果,便是城镇(含矿区、港口)市民阶层的勃兴。两宋文献中的“富商巨贾”、“冶家”、“磨户”、“茶培主”,还有“行老”、“市头”(以上为一方),以及“杂作工匠”、“裨商细贩”、“百姓绣夫”、“游手末作”(以上为另一方)等,就是这个阶层的基本成份。就是被人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之重要表现的市民、矿工斗争,宋代亦有端倪可鉴。前述井研县“佣身赁力”之盐工一不如意就“递相扇诱,群党哗噪”可算经济斗争;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安徽舒州宿松矿工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有众五百余”②则是武装斗争性质了。如所周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结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基础性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雇佣关系发展和市民阶层初兴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视为原始工业化赖以启动的社会条件。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条件的共同支撑,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才会取得如上所述的种种进展。遗憾的是这个进程并未结出现代化之正果,直接的原因当然可以归之于战争的干扰。12世纪初女真铁骑频频南下,饮马黄河;接踵而来的13世纪由蒙金战争拉开帷幕,继之以宋蒙(元)战争,中原、江南屡遭战祸蹂躏。其后虽在元朝统治下复归统一,但领主分封制、匠局制(实即工奴制)和“驱口”、“人市”等前封建制因素在更广阔的地域内死灰复燃(原先大致局限在辽夏金辖区),要到明初开国数十年才重新回到宋代开启的历史轨道上来。这就是说,自北宋末年开始,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段内,原始工业化进程因屡遭打击而奄奄一息
代宗时期铸造一贯钱成本是两贯,私人把铜钱融了卖铜又能得几倍的利润,铜钱面值为啥比原材料还低这么多,不应该啊,再贬值也不应该比原材料价值低啊。对货币史一窍不通,求别拍。
cmlj:铜钱不是全铜的。
陈汤再世王世杰:小说里说的很清楚啊,铸钱的成本可不是单单原材料,造炉子要花钱,雇佣工人要花钱,还有负责的官员要开工资,造好了你运到国库里也要花钱。所以一贯钱的成本两贯不足为奇,就是这样唐朝还在不停地用二倍的成本铸钱,直到灭亡,为了应付钱荒。
茗夜雨:别说古代,就是现代,老一毛和五毛的硬币也没有原料值钱。钱比原料值钱那是到了纸币时代才实现的,当然,你足够黑的话掺其他原料也可以实现......
bairao:1、铜的总供应不足;2、这导致铜和钱不能同时满足需求;3、政府更看重铜钱作为货币的功能;4、钱多了铜就少,政府又要优先保证钱的供应,因此一方面是政府在承担把钱维持在相对较低价格的成本,另一方面铜的价格也正是因为政府控制供应而上涨;5、如果政府不积极铸钱,钱的价格就会高涨,一方面导致钱荒影响贸易流通,另一方面又会出现私铸的问题,并引发钱币的劣币化。
深潜者:他们为啥不铸大钱,然后坚定的维持大钱的价值呢?
monitor:感觉与中国古代其实多个货币同时流通有关。比如五铢钱流行了很久。如果朝廷货币实际含铜太低,百姓会拒绝使用。就像明清时期中国还有西班牙的银币流通。
深潜者:只要朝廷接受按照大钱面值支付的赋税,那么大钱的流通就不可能被拒绝呀。
monitor:回到楼主的问题,其实我国就是天然通缩的。铜矿经过常年开采,加上海昏侯这种埋进去几吨铜钱的人很多,铜矿越来越少。朝廷的铸币权其实是残废的。难道你能制止下面官吏只收小钱,然后转成大钱上交么?
御驾亲征永历帝:还有货币外流和窖藏铜钱的问题,我觉得这比铜矿开采的问题还严重?
monitor:外流应该不严重,毕竟我国主要是出口。
可怕的鸭骨头:铜钱本身就是出口商品。
御驾亲征永历帝:不严重?比如宋朝铜钱外流“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是有名的。引用两段:“宋代官府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钱禁’,曾规定携带铜钱五贯以上出境者就要被判处死刑。后来边境形势紧张,刑罚加剧,规定携带铜钱出西北边境一贯以上者就要处死。“钱禁”涉及了各个地区,包括京师。为了防止都城“钱荒”,无论是北宋的汴梁还是南宋的临安,都颁布了禁令,咸平三年“仍令开封府出榜晓谕,其诸城门锁不得私放出见钱。”朝廷也对官僚机构下了禁令,一律不得搬运铜钱下海船,防止官员假借公事名义走私铜钱。除了海防,边防合法的交易通道也被堵死。官方如向边关地区百姓买马,不得再用铜钱,而是改用布帛或者茶叶等实物交换。只是,多头管制之下,铜钱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出宋代的国土,“钱禁”还是失禁了。”“据统计,日本出土的唐至清代中后期的中国货币约达260余万枚。据日本学者入田整三的分类分析,在日本全国18个地方出土的554714枚钱币中,以北宋钱的种类、数量最多,约占81.9%,其余依次为唐钱8.6%、明钱7.3%、南宋钱1.4%、其他0.8%。据史载,永乐年间,明成祖两次赐给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铜钱1700万枚。成化年问,明朝又赐予日本来贡者铜钱5000万枚。中国铜钱的出土地点遍及日本列岛,在新滂县,出土千枚以上钱的地点达30多个。”
我开拖拉机:那私铸铜钱的利润从哪里来?
vichywasser:劣钱啊,官造一文可能含铜80,私造的铜20,这不就是利润吗。还有模具啊,人工啊,反正能低就低。
陈汤再世王世杰:外流从唐就很严重,因为只要你的结算货币是中国的,就不可能不外流。
vichywasser:贵金属货币都避不开这个问题吧,最后只能把贵金属放央行做准备金发纸币吧。
时之沙漏:铜原料涨价了吧。铜钱的表面购买力低于铜材料的价格。那么毁钱铸造器就有利可图。
铁木辛哥:其实那是古代行政效率低下导致的。一钱3铜7锡铅,除非王朝末期物价飞涨铜价高于币值3倍以上,否则人干融钱的事情。其实这部分和融掉黄金首饰的原理一样。如果金价涨了,才有融首饰的意义,否则是没意义的。
古代金融知识不如现在这么充足啊。其实古代铸钱绝对是超级划算的买卖,为什么吴王刘濞有反汉的资本,就是因为可以自己铸钱,铸币税大大的。所谓铸钱亏本,纯粹是政府已经腐败SB到不行的结果而已。
不是我国天然通缩,而是金属货币本身就有天然通缩的属性。
zyxssboy:贵金属,贵金属,都加了一个贵字,使用价值自然也是极高的。既有极高的使用价值,又有很好的流通价值,天然就会造成资源稀缺,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纸币出现之前,简直就是无解。
petrus:其实说穿了很简单,自然经济体制下的官僚系统不懂也不知道怎么维持币值,相反,为了维持稳定,他们还要人为打压币值。在自然经济体系下,铜钱的价值其实很高,所以早期铸钱很有利润,但是在生产能力不断增长,流通大大增加以后,本来作为实物交换补充的贵金属货币,慢慢变成流通主力了,这时候要么随着商品量大量增加而贵金属货币价值随之大增,同时伴随通货紧缩,要么拼命铸币,用发行量弥补流通缺口,阻止通货紧缩的出现,但这时候伴随的是货币原料价值与货币交换价值的倒挂。对自然经济体制下的官僚来说,维持国家统治,增长税收,自然是用国家货币最方便,什么贯石匹两束,其实只有贯是最好使最方便的,而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强烈需求货币供应量,而官僚们又不会计算经济总量与货币发行量与货币本身价值之间的关系,那就只有忍受价值倒挂,拼命砸成本维持货币供应量呗。
注:本文所有均来源于网络。
本文作者:在祀与戎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